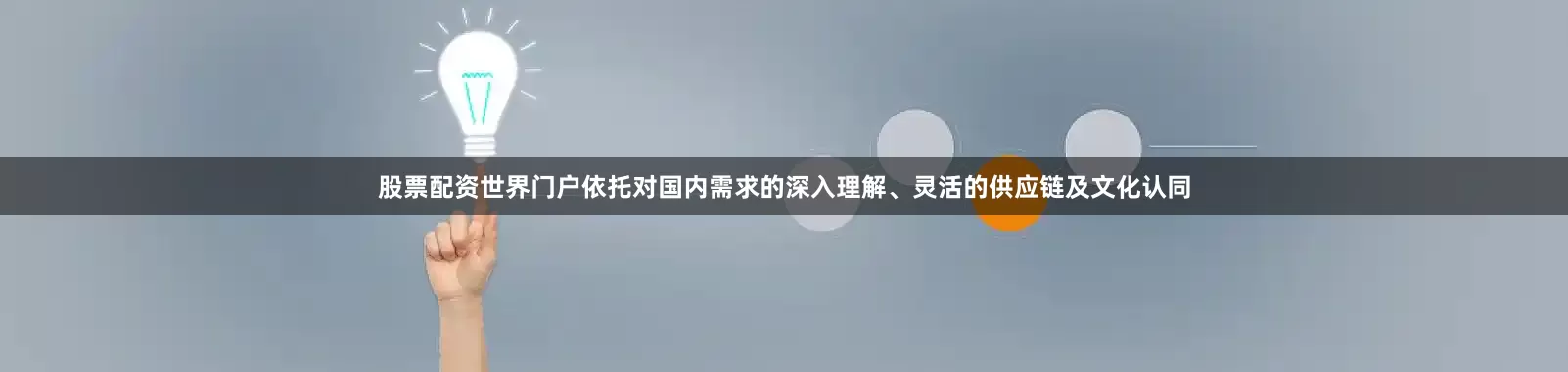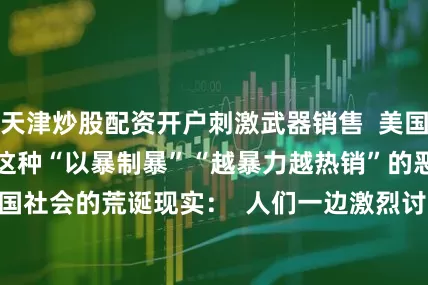作品声明:内容取材于网络
乾隆年间,一个六岁的女童,因为被选为公主的伴读,从此命运彻底改写。
她聪慧知礼,温婉端庄,不仅赢得了十公主的喜爱,更在不经意间,被天下权势最高的皇帝看在眼中。
岁月更替,她从宫女、福晋、贵妃一路扶摇直上,最终登上皇后宝座,统领六宫五十四年。
她是谁?又如何在深宫之中步步为营、赢得人心?
小伴读入宫乾隆四十年,紫禁城内,宫人奔走传信,满宫张灯结彩,乾隆的第十位公主诞生了,固伦和孝公主,亦是他最晚年得来的掌上明珠。
展开剩余92%那年,乾隆年事已高,却因这个小女儿重燃亲情的柔情。
他亲自为她赐名,选最稳重的嬷嬷照料起居,甚至每日抽空看望几次,几乎做到了皇帝身为父亲所能做到的极致。
而在京城西北的一处幽深胡同内,另一户满族人家的生活却是截然不同的光景。
这个姓钮祜禄的八旗子弟家庭,原本也曾显赫一时。
她的曾祖、祖父皆是朝中官员,家族中也不乏出将入相之人。
但世道轮转,人丁兴旺之后,靠祖上的功名也逐渐吃紧。
这个钮祜禄氏家的长女,从小便早熟懂事,她不像寻常女孩般柔弱懒散,年纪虽小,却已学会照顾弟妹,见人行礼不失规矩。
正因如此,在乾隆为十公主挑选伴读之际,宫里太监奉旨四处寻访聪明机警的女孩。
经过一番层层筛选,钮祜禄氏因年纪相仿、家世尚可、品行出众而被提名进宫。
初入皇宫,她没有因陌生的规矩和森严的礼制慌乱。
反而总能迅速领会要点,一丝不苟地完成规定动作。
才入宫不久,就已能准确记住御花园的门道、宫女们的轮值顺序,还主动帮衬其他年幼的宫女叠衣整理案几,言语温和不逾矩,深得年长宫人喜欢。
乾隆初次见到她,是在养心殿外的暖阁之中。
那日他正在与十公主共进午膳,而小女孩就在公主身后恭敬侍立。
十公主嚷嚷着要她背一段《千字文》,小女孩低头应了声“是”,便稚声稚气地念了起来,却字字清晰,声调平稳。
乾隆起初并未在意,待她背完之后,竟笑出声来:“年纪小小,倒也有几分学问。”
他略感兴趣,便叫她上前说话。
小钮祜禄氏跪拜得体,不卑不亢。
乾隆问她父亲做什么,她如实答:“家父在市坊卖纸笔。”
语气中既无羞涩,也无怨气,反倒多了几分坦然。
此后,她便被钦定为十公主的伴读女童,正式留在宫中,而从这一刻起,她的命运,也悄然改写。
成为伴读后,她不仅要学习诵读诗文,更要陪着十公主日常起居。
每日卯时起床,午时前完成读书、抄写、礼仪训练。
十公主性子活泼爱玩,但凡去哪儿,必喊着小伴读一道前往,她如影随形,既是陪伴者,也是隐形的镜子,时时自省。
她的聪明不在夸夸其谈,而在于分寸,该退时不抢,该进时不怯。
这份温婉沉静,恰是宫中最为稀缺的品格。
每逢节日,公主携伴前去太后宫中请安,钮祜禄氏一板一眼行礼,从未出错。
太后看在眼里,也道一句“稳重”。
可她自己却始终安守本分,不骄不躁,她年纪虽小,已明“宫中无小事”之理,事事谨慎,处处留心。
就这样,钮祜禄氏在宫中逐渐扎稳脚跟,而她在十公主与乾隆之间的频繁露面,也为她后来的命运,埋下了伏笔。
变身皇子福晋乾隆五十七年,紫禁城内开始酝酿着一场重要的选秀。
彼时的钮祜禄氏已年方十四,伴读之职早已结束,却因多年来在宫中表现出众,被列入候选名单之中。
这场选秀,不同寻常,它是专为嘉亲王颙琰而设。
颙琰,乾隆的十五子,早在乾隆三十八年便被秘密立储。
此刻的颙琰,虽已娶嫡福晋喜塔腊氏,并育有嫡子绵宁,但因福晋久病体弱,皇子尚小,乾隆帝便意图再为其增选一名侧福晋,以安王府内院。
十公主得知此事后,率先推荐了自己的旧伴读,钮祜禄氏。
乾隆想起那张清秀安静的小脸,不禁点头:“这丫头,倒也识大体。”
就这样,在没有太多喧嚣的背景中,钮祜禄氏便被钦点为嘉亲王侧福晋,离开了她熟悉多年的后宫,步入了王府的新天地。
初入嘉亲王府,钮祜禄氏的身份不过是“侧福晋”,在清代礼制中,仅次于嫡福晋,名分虽正,却无实权。
王府内妾室众多,斗气暗涌,她这个“新来的”,又不是权贵之女,自然不被看好。
喜塔腊氏虽为嫡福晋,却久卧病榻,王府上下无人真正执掌中馈。
钮祜禄氏不声不响,默默学习府内事务,从请安送礼到安排节庆,她皆亲力亲为,不曾倚仗“公主推荐”的光环。
她在后宅中将一切安排得妥当周全,屋内屋外井井有条。
就连颙琰的心中,这位侧福晋也悄然占据了一席之地。
起初,颙琰对还算年幼的妾室并无特别之意。
她不似别的女人那般急功近利,也从不在他跟前撒娇邀宠,可偏偏这般不争,反让他心生好感。
与王府的复杂相比,钮祜禄氏更在意的是颙琰的嫡子,绵宁。
绵宁幼年聪颖,却因母亲病重,时常独自玩耍,她不是其生母,却待其如己出。
绵宁最初对她称“钮侧福晋”,不久后便改口叫她“额娘”。
嘉亲王颙琰得知后,并未责怪。
乾隆六十年,钮祜禄氏生下颙琰的第三个儿子,绵恺。
她不仅“母凭子贵”,被嘉庆提为贵妃,更因此一步步走入帝后的轨道。
自此,她不再只是那个曾为公主伴读的小宫女,也不只是安于王府一隅的侧福晋。
她开始参与内廷事务,打理中馈、掌管礼仪,连宫中都传来了她贤良持家的名声。
而她的父亲恭阿拉,也因女儿之贵,被提拔为从三品官职,一家人总算过上安稳光景。
可这位钮祜禄氏依旧不骄不躁。
凤冠加身乾隆六十年,当年的英武皇帝早已白发苍苍,却依旧精神矍铄。
他虽早已决定退位,却不愿舍去“太上皇”的尊号与权力。
彼时的乾隆,虽让皇子颙琰登基为帝,改元嘉庆,但宫中宫外谁都明白,这座帝国的真正舵手,依旧坐在那座养心殿里。
正是在这个微妙的交接时刻,钮祜禄氏迎来了人生的又一次跃迁。
嘉庆元年正月初四,皇帝刚刚继位第四日,便下旨册封她为“贵妃”。
这道圣旨不是单纯的礼数,而是朝廷对她多年来德行的肯定。
而让这段荣宠更进一步的,是嘉庆二年那场突如其来的丧礼。
皇后喜塔腊氏因久病无愈,不幸崩逝,享年不过三十余,消息传出,整个内廷哀悼不已。
皇后之位空悬,皇帝需要一位能稳定后宫、替他料理内务的中宫之主,诸妃中,惟钮祜禄氏最为合适。
这一次,册立未如往常那般仓促行礼,而是遵循太上皇定下的规制,需守先皇后丧期二十七月后,方可行册立大典。
于是在嘉庆二年,她先被晋封为“皇贵妃”,暂摄六宫之政,直到嘉庆六年正式立为皇后,移居储秀宫。
这期间,六宫之中风起云涌。
皇贵妃位高权重,又年纪不大,朝中有人言她“受太上皇之恩,恩宠深厚”。
宫中也有旧妃暗中讥讽:“出身寒微,焉能掌后宫?”
她听得多,却从未回过一句,只以实际行动回应流言。
她每日亲自督查各宫膳食衣物,遇嬷嬷懈怠、宫人失仪者,严加整肃,却不妄加责罚。
她懂得分寸之道,也知人心之险,凡事不过三言两语,言简意赅,令人既敬又畏。
后宫中最怕的不是严厉,而是偏私,而她,最不偏私。
她对前皇后的嫡子绵宁,一如既往地关怀备至,绵宁幼年时,常唤她“钮额娘”,如今仍亲近如初。
这份胸襟,是旁人学不来的。
嘉庆六年,紫禁城里张灯结彩,金凤高悬。
大典那日,百官齐聚,六宫列队,她身披霞帔凤袍,头戴九凤冠,一步一跪,缓缓登上坤宁宫宝座,凤印加身。
那一刻,她终于成为了真正的“中宫之主”。
作为皇后,她必须打理六宫、统筹内务、辅佐皇帝,还要维护宫中数百人的衣食秩序。
她每日在景仁宫与储秀宫之间来回,查账目、阅奏本、批宫务,忙到深夜不曾休息。
嘉庆虽不似其父那般精于政事,但对她却极为信任。
朝中大臣奏事涉内廷者,往往要“请中宫裁定”,绵宁生病,她亲自侍药。
她不是凤凰中最耀眼的那一只,却是羽翼最坚韧、飞得最长久的那一只。
垂帘幕后,定鼎储君嘉庆二十五年,皇城传来噩耗,嘉庆皇帝猝然驾崩,消息自山庄传回京师,一石激起千层浪。
紫禁城沉入一片凝重之中,内务府连夜进宫禀告,太监奔走,宫门闭锁,百官静候遗诏。
宫中嫔妃宫女无不惊恐失措,仿佛一夜间,帝国失去了心脏的跳动。
此时,掌中枢、握六宫、又年届半百的皇后钮祜禄氏,听闻皇帝驾崩,虽神情沉痛,却未有丝毫慌乱,从寿康宫到皇宫正殿,她一路未言。
皇帝骤亡,继承人尚未公布,朝堂上下尚未有定策之人。
稍有不慎,便可能酿成储位之争,乱起朝野。
按照清朝“家法”,皇帝在生前若已秘密立储,遗诏会藏于乾清宫“正大光明”匾额之后,亦有副本封入金匣,由亲信随身保管。
但在嘉庆突然崩逝之后,无人知晓密诏何在,太监翻遍了乾清宫、景仁宫、养心殿,皆未有所获。
群龙无首之际,有人开始低声议论,“太后有二子,皆出嘉庆,是否……”
声虽微,却如风中毒草,极易蔓延成灾。
钮祜禄氏没有急于召见百官,也没有将自己的儿子绵恺或绵忻召回宫中,而是命人火速前往承德,寻找皇帝随身之物。
大臣们心知肚明,若太后有意让自己的亲子继位,此刻大可下旨“立子承统”,却并未如此,可见其心志之清明。
两日后,承德飞马急传回金匣密诏,诏中赫然写明:
“皇次子绵宁,承朕衣钵,继统大清。”
一锤定音,太后只点头一言:“照旨。”
那一刻,她将本可据为己有的权力,亲手交出,她的儿子未登大位,却毫无怨言,而她本人,也因此举,被朝中文武一致称为“贤后”。
自此,钮祜禄氏尊为“恭慈皇太后”,彻底走入幕后,却并未退出政事。
道光皇帝初登大位,虽为嫡子,但政治经验尚浅,军国大事仍需请安问策。
钮祜禄氏每日清晨必起,按时接见皇帝,叮嘱之言从不溢美,亦不纵容。
这种分寸,她拿捏得恰到好处。
她在宫中威望极高,太监宫女皆称她“太后娘娘明断如镜”,后宫六宫妃嫔众多,却无人敢造次。
她历乾隆、嘉庆、道光三朝,从十公主伴读,到侧福晋、贵妃、皇后、太后,走过风雨五十余载。
这就是她的一生。
发布于:山东省牛达人配资-牛达人配资官网-全国股票配资平台-配资指数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在线配资流程摄像头区域则是挖孔设计
- 下一篇:没有了